原发性肝癌(主要指肝细胞癌,HCC)是一种全球性疾病,是世界第二大癌症相关死亡的病因,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仍在不断攀升,预计至年,每年将会有超过万的新发HCC病例。中国是肝癌大国,全世界55%的肝癌在中国,且由于中国大多数的肝癌患者是出现症状后才去就诊,因此在确诊时往往处于晚期,丧失了最佳的根治性治疗机会,如接受手术切除、肝移植以及局部消融等。除上述的根治性治疗方案外,HCC的辅助治疗还包括肝动脉介入化学栓塞、全身化疗、放射治疗、分子靶向药物治疗、以及当前逐渐兴起的生物治疗和免疫治疗。然而,HCC对大部分的标准化疗方案均不敏感,放射治疗的效果也非常有限。索拉菲尼是来自于基础转化研究的具有开创性成果的新型药物,被证实在晚期HCC中有效,并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被美国食品药品批准用于晚期HCC的分子靶向药物。尽管其对患者总体生存率的提高作用有限(中位生存时间仅延长3个月左右),但是这却给其他更多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应用带来了希望。然而,近年来,舒尼替尼、布立尼布、依维莫司等其它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在晚期HCC中的III期临床试验的表现均不理想。总而言之,目前在转化医学领域,尤其是从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肝癌方面进展尚未发生突破性进展。从向临床转化的角度分析,当前原发性肝癌相关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1)探索用于早期诊断的生物学标记物;2)探求分子标记与影像学、组织学特征的相关性;3)鉴定新药物靶标和探索基于肿瘤生物学特性的个体化疗法。本文主要探讨HCC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进展,对可能实现临床应用转化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一、HCC的早期诊断方法
HCC是唯一的不需要获得组织学证据就可以确诊的实体肿瘤类型。最新版本的欧美肝病学会指南中指出:如一个肝硬化患者出现新生肝脏结节病灶,并符合“快进快出”的影像学特征表现,即可确诊HCC。但该病灶直径超过2cm时,无论行肝脏断层成像CT还是肝脏MRI检查,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表现较好。然而,倘若病灶小于2cm,其CT和MRI的检测效能将会有所降低,其假阳性率可达20%。
除CT和MRI外,超声对比增强造影检查(CEUS)也是目前被认可的一种诊断HCC的影像学方法。在97%的合并肝硬化的HCC患者中,CEUS诊断HCC的总体准确性可以达到80%。研究表明,CEUS可以通过肿瘤内血管成像提示肿瘤的分化程度。但由于存在将肝内胆管癌误诊为HCC的风险,CEUS尚未被主流学会纳入至HCC的诊断标准中。尽管影像学技术日趋成熟,但仍有小部分病例呈现为异型性影像学特征,因此单独的影像学检查不能做出诊断。
组织活检是传统的HCC诊断方法之一,常用于超过1cm、伴有不典型影像学特征的可疑肝脏结节病灶的诊断。有研究显示直径在1-2cm的病灶中,近50%的病灶是影像学检查无法明确的。常规组织活检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肿瘤的针迹播散,一项纳入超过0例病例的研究报道其发生率为0.76%,另一项研究纳入8项荟萃分析后报道其发生率为2.7%。肝组织活检的另一风险是出血,其发生率较低,约为0.1-0.01%。病灶大小为1~2cm的患者,多数医生选择影像学观察随访,当病灶达到2cm时,病灶即呈现为典型的影像学特征。此外,对小于1cm的HCC病灶,由于距穿刺表面较远难以定位且肿瘤组织分化常常较好,诊断的假阴性率高。
一种新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关键在于利用已有的临床标本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以确认标志物,无需等到后期大型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才得到最终结果。然而,HCC组织标本的缺乏阻碍了标志物的研究,延缓了HCC个体化治疗的发展。部分研究者认为在缺乏已知的生物标志物与分子亚型的条件下对患者进行活检是缺乏职业道德的,而另外Torbenson等则认为HCC活检的应用,尤其是在临床试验中,有利于发现新的标志物和促进个体化靶向治疗的发展。
在乳腺癌的临床试验中,Parker等利用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等生物标志物的富集可使临床试验失败风险降低50%,并可节省27%的费用。在未来的临床试验设计中,研究者可以将肿瘤组织活检纳入试验方案中,更为有效地对靶向药物靶点的表达情况进行评估。类似的研究已经开展,在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MET)抑制剂替万替尼(Tivantinib)治疗晚期HCC的II期临床试验中,研究者通过组织活检获取肿瘤组织并利用免疫组化评估MET的表达量。随后的治疗结果显示,只有在MET高表达患者中获得了生存率的提高。II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若以上发现得到证实,未来对于接受替万替尼治疗的患者有必要行肿瘤组织活检评估MET表达情况,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类似临床试验的开展有助于更多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提高肿瘤组织活检的临床应用,从而推动个体化治疗。
二、分子靶向治疗
BCLC分期不仅对HCC进行分期,它也是唯一提供了每个阶段的治疗建议和最佳治疗方案的分期标准。然而BCLC分期并非被广泛接受,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由于中晚期肝癌患者比例较高,如果遵循治疗方案偏保守的BCLC分期,将会导致很多的患者失去手术机会。而关于BCLC分期治疗指南的争议,主要集中在BCLC中期患者治疗方法的选择上,包括单个肿瘤(5cm)到弥漫浸润性肿瘤、肝功能Child分级A到B级的病人。BCLC分期建议该期患者行动脉栓塞化疗(TACE),然而有研究显示肿瘤局限性较大的中期HCC患者仍可以接受手术治疗,一些中心成功地对超过米兰标准的中期HCC患者进行了肝移植。无法接受TACE治疗的患者也可行索拉菲尼疗法或其他疗法包括射频消融、Y90化疗、立体定向放疗,这些治疗方法已经常规应用于HCC的治疗中,但由于缺乏高质量证据的支持,尚未纳入至巴塞罗那分期中。对BCLC中期患者进一步分级以优化处理建议的研究已经开展。随着治疗HBV和HCV新药的出现,未来HCC临床分级的降级或许可以实现,这将会改变现行的治疗模式,例如推动移植术向肝切除术或消融的转变。接下来将介绍基因改变和分子通路异常调节在HCC基础研究中的进展,这些进展有助于新靶点的识别和靶向药物的研发。
1.抗血管生成药物——索拉非尼HCC是高度血管化的肿瘤,其血供主要来自肝动脉,因此血管生成是HCC治疗中的主要靶点之一。通道相关生长因子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胰岛素样生长素-1(IGF-1),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转化生长因子(TGFβ)等均促进了HCC中血管的生成。索拉菲尼通过阻断多种酪氨酸激酶受体如VEGFR和PDGFR以阻断信号转导通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肿瘤血管生成,从而达到抗肿瘤的目的。但很多患者由于出现不良反应以及耐药性而无法进一步接受治疗。因此准确预测疗效和避免不良反应是索拉菲尼的研究热点之一,多种生物标志物已被证实可预测索拉菲尼的疗效。Arao等报道在第11号染色体上FGF3/FGF4片段的扩增极大提高了肿瘤对索拉菲尼的敏感性。Horwitz等研究表明包含VEGF-A片段扩增的HCC在索拉菲尼治疗后患者生存率显著提高。该研究显示VEGF-A和VEGF-C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肿瘤的进展、患者的生存率相关,pERK和VFGFR-2的高表达则提示索拉菲尼治疗该类晚期患者效果不佳。提高HCC对索拉菲尼敏感性的研究尚在进行中,结果值得期待。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沉默促细胞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4(Mapk14)可以提高HCC对索拉菲尼的敏感性,未来合并Mapk14阻断的索拉菲尼疗法可能解决其耐药性问题。
2.MET抑制剂——替尼万尼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及其受体(c-MET)在HCC的进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MET是目前唯一已知的HGF受体,研究显示MET基因的表达与血管侵犯及不良预后(如肿瘤快速扩散和生存期缩短)有关。替万替尼(Tivantinib)是一种口服选择性MET抑制剂,阻断MET受体,使其构象失活并阻断下游信号转导。在晚期HCC患者的二期临床试验中已显示出有前景的抗肿瘤活性,且只有在MET过表达组才能获得生存率的提高,因此MET成为第一个晚期HCC靶向治疗的分子学生物标志物。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进行替尼万尼用于之前接受过索拉菲尼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治疗的三期临床试验。
3.mTOR抑制剂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转导通路参与了肿瘤细胞中的炎症、自体吞噬和血管生成的调控,Yao等报道在40%-50%的HCC中出现该通路的上调,并与血管侵犯、肿瘤复发和不良预后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一项3期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中,依维莫司并未提高晚期HCC患者的生存率。尽管如此,考虑到临床前期数据支持mTOR途径在HCC中的作用这一证据,评价西罗莫司在预防HCC移植后的临床试验和第二代mTOR阻断剂如坦西莫司、TORC1/TORC2双阻断剂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4.其他分子靶标研究人员最近发现端粒酶逆转录酶(TERT)突变是HCC中最为常见的体细胞突变,发生率为40%-60%。这些突变也出现在异型增生性小结节和肝腺瘤中,研究者认为认为是潜在的驱动突变。小分子TERT阻断剂目前正应用于乳腺癌和肺癌的早期临床试验中,实验结果值得期待。Wnt信号通路各蛋白表达水平改变及相关基因突变参与了HCC的发生,Guichard等人研究发现,在30%-44%的HCC中β-catenin的突变激活,B—catenin及其下游靶基因的激活与人类某些肿瘤的发生有关,他们的过度表达可导致肿瘤。而非经典Wnt途径相关基因如AXIN1和AXIN2在少部分HCC中也会发生突变。除了突变激活,Wnt通路在HCC的发生中还通过其他的机制发挥作用,包括TGF-β的激活,Wnt3a的上调以及frizzled受体的过表达。因此,Wnt通路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Gao等利用抗体作用于GPC3阻断Wnt通路获得了理想的结果。TGF-β通路的激活存在于一部分HCC中,TGF-β通路的激活能够促进肿瘤血管的生成、促进上皮间质转变(EMT)、调节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效应,最终促进了肿瘤的进展和转移,因此是理想的治疗靶点。目前已有TGF-β抑制剂进入临床研究,TGF-β受体抑制剂LY在2期临床试验中显示有效,正处于3期临床试验阶段。
三、HCC免疫疗法
在调节原发性肝癌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免疫机制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肝硬化患者进展至HCC过程中,由此引发的免疫反应相当复杂,肿瘤免疫耐受以及肿瘤诱导产生的抗肿瘤免疫均会发生。HCC的肿瘤免疫耐受机制包含了调节性T细胞数量的上调,Fu等研究发现在肝癌患者体内,调节性T细胞的增高,提示其不良预后。
HCC的免疫学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了解癌症的免疫学机制,从而探究新的治疗策略。目前,多种免疫疗法处于研究阶段,部分疗法已进入临床1-2期试验。作用于肿瘤相关抗原如甲胎蛋白、端粒酶转录酶、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完成,但临床效果尚不理想。针对多肿瘤相关抗原靶点并利用创新技术如计算机引导的表位优化设计疫苗,有利于提升抗肿瘤疫苗的效果。最近一项临床试验研究报告显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纳武单抗在晚期HCC患者中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且无显著毒性,缓解了人们对免疫检查点阻断剂会引起病毒感染的担忧。肝脏肿瘤微环境中存在着多种免疫抑制机制,以上策略的结合最终或许能提高临床疗效。
总论
HCC在流行病学水平和分子水平上的异质性是临床医生在诊治中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原本索拉菲尼的出现给更多其他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潜在应用于HCC带来了希望,但多种分子靶向药物的III期临床试验结果均不理想。目前在HCC基因和分子领域的研究或许能够促进更有意义的HCC分级系统产生,并有助于实现基于肿瘤生物学的个体化治疗。随着研究者对于HCC发病机理的理解不断加深,未来更多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药物靶点的识别,最终促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向临床的转化,从而改善HCC患者的预后。
赞赏
人赞赏
北京中医白癜风医学研究院怎么样皮肤病治疗最好的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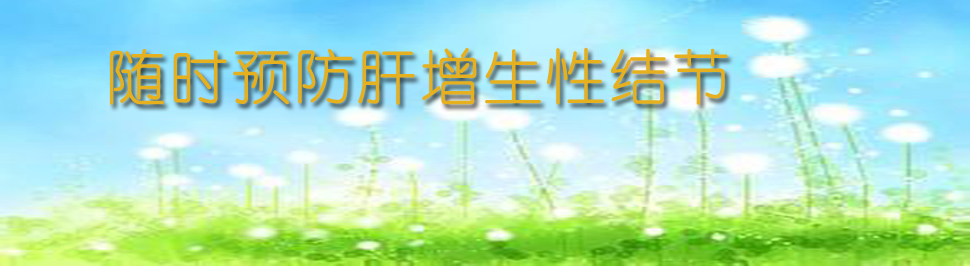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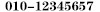 E-Mail:
E-Mail: